当前位置:首页 > 商业/管理/HR > 人事档案/员工关系 > 国家意志下的人性扭曲论《芙蓉镇》中秦书田王秋赫的人物形象
国家意志下的人性扭曲——论《芙蓉镇》中秦书田、王秋赫的人物形象《芙蓉镇》作为“反思文学”的翘楚(荣获代表主流文化的第一届茅盾文学奖),描写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极左路线破坏下的中国农村生活的变迁。整部小说融入了人物命运、历史变迁和乡村爱情于一体,构成了一幅广阔的当代农村的社会风俗画。正如古华在自序中所说到的这是在“唱一曲严峻的乡村牧歌”。小说中着重描写了在“文革”前后十多年中“左”倾思潮横行时期赤裸裸的社会现实,感叹中国普通老百姓在那人妖颠倒的年代里悲苦的命运和被扭曲的灵魂,无情地抨击了极左路线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在极左的国家意志下,人性被扭曲,而人性的扭曲则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在个人无法抗拒的“左”祸高压下不得已而扭曲以得以生存;另一种则是自觉扭曲自己的人格,以适应外在的高压,并且从中谋取到自己的利益。前者以《芙蓉镇》中的秦书田为代表,后者则以王秋赫为代表。一、秦书田:含泪在笑的“疯癫”者秦书田在小说《芙蓉镇》中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文艺青年,对自己所从事的文艺事业充满了激情,只因搜集流行于湘西民间的风俗歌舞《喜满堂》而被划为“右派分子”被遣送回原籍监督劳动改造,在改造期间他“老实伏罪”,发挥他音乐的歪才,写出了《五类分子歌》还要求在大队召集的训话会上歌唱。他总是一副乐天派,不仅请求上级给他改成分而且非常服从管教,当上了五类分子的小头目后,每逢大队召集五类分子作汇报和训话时,只要一声“秦癫子”他就会立即响亮答应一声:“有!”并像学堂里的体育老师那样半臂半屈在腰间摆动着小跑前来,直接跑到党支部面前脚后跟一并,来一个“立正”的姿势,右手巴掌平举齐眉敬个礼:“报告上级坏分子秦书田到!”接着低下脑壳,表示老实伏罪。秦书田总是乐观地在夹缝中生存着,不过后来因递上了与胡玉音结婚申请书招致判决十年徒刑。在批判台上他给胡玉音说的话是“活下去,像牲口一样活下去。”从秦书田对胡玉音说的最后一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秦书田信奉“好死不如赖活着”,只要活着就有希望,秦书田始终是个清醒者,他深知当时环境的恶劣,他只能用“黑色幽默”的方式来自我解嘲。秦书田表面自轻自贱,玩世不恭,戏虐调侃,不将挨批斗当一回事,整天笑咪咪的,劳动改造时他竟然跳起了扫街舞。但是如果我们深究其内心世界又发现存在着外表表象与内心本质的尖锐矛盾。正如书中所说的“莫看他白天笑呵呵的,锣鼓点子不离手,山调小调不断腔,晚上却躲在草里哭,三十几岁一条光棍加一顶坏帽子,哭得好伤心。还有民兵晚上在芙蓉边站哨,多次见到他在崖岸上走过来走过去,大概是在思索着他的过去和将来的一些事情。”秦书田的一言一行让我们可以看到他内心的苦闷,他要求做人的尊严,呼唤正常的生活,渴求幸福的爱情和家庭。但是,在当时社会没有人能够理解他,一场政治运动扭曲了他的性格,生存的信念支撑他孤独痛苦的灵魂,只能以“穷开心,浪快乐!”来捂住汩汩流血的伤口,不得不戴上面具做人,在人前装笑脸接受凌辱,在人后只能偷偷落泪。一个富有才气的知识分子被剥夺了独立的意志,被阉割了自由的灵魂。秦书田时时刻刻都是一个清醒者,他既明白是非黑白,内心也隐藏着一颗赤诚之心,充满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他从不动摇自己对党的信念,坚信自己是无罪的,他从没有承认自己反过党和人民,宁愿被扣上坏分子的帽子。他只字不提“右派”分子也从不分析“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但他又意识到当前自己所处的环境的恶劣,面对极左势力的摧残,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他只能把一颗痛苦的心埋藏起来,以戏谑调侃的甚至癫狂变态的方式缓解内心的苦闷,忍受痛苦是为了抒发自己极度的悲哀,是为了更好的活下去。但他也坚持自己的原则,在公社因与胡玉音申请结婚而惨遭批判时,王秋赫让他跪时,他第一次直起腰骨,不肯跪下,甚至不肯低头,因为“过去命令他下跪的是政治,今天喝叫他下跪的是淫欲”。他的“癫狂”其实是一种生存的智慧,斗争的艺术。他才是一位真正的胜利者,是一个掌握一定艺术技能的现代知识分子对荒诞疯狂的强权政治的一种曲折隐晦的反抗。秦书田的戏剧人生实乃是一种特殊形态的积极人生态度。他不像北大女学生林昭的那样铮铮铁骨,林昭在被划为右派送去劳教,但她拒不认罪后被枪杀,到了1980年才被平反,她是以自己的壮志情怀和鲜血捍卫了历史的公正。秦书田为了在那个“红色”恐怖笼罩中国大地的非常时期更好的活下去,他并没有选择“士可杀不可辱”而是一直忍辱负重,像司马迁那样为了完成《史记》在受完宫刑以后毅然选择“苟活”,像“牲口一样活下去”。他一直拿自己寻开心,用以排解内心的苦闷,他的嘲笑并不是对自己,而是嘲笑的是以逼人们自我凌辱和将人身侮辱视为阶级斗争重要手段的荒唐年代。他的苟活将一切斗争戏剧化了,他一直在笑,但我们可以深深地体会到他是在含泪在笑。秦书田的笑和疯癫只不过是一种生活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最积极的生活态度。二,王秋赫:政治运动中可怜的疯狂追捧者王秋赫是在旧社会中失去土地从而成为游民无产者,以及新社会里对各种政治运动的热衷者。他是一群人的代表,是典型的农村流氓无产者。毛泽东曾说:“这种人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之一。这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是很有破坏性,如果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而在当时的愚昧时代里,王秋赫就是属于没有“引导得法”而对社会具有极大的破坏性的人。芙蓉镇》中的王秋赫是个十足成色的无产阶级,黄金无瑕,麒麟无真,查他的五服三代,他的父母全没有出处,简直可以和鲁迅笔下的阿Q相媲美。他从小蹲祠堂,住祠堂,长大以后就给祠堂跑腿办事,供财主老倌随意驱使,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就被工作队选为“土改根子”并且还把他作为忠诚可靠的骨干,去一户地主看守浮财。如果不是他违法乱纪,他早就被工作队提拔成脱产干部了。虽说这样,土改工作队仍然看他“根正苗红”给了他许多东西包括镇中唯一的一座高大精美的建筑——吊脚楼。然而,他仍不吸取教训,好好地改造,反而带着旧社会时养成的恶习继续好逸恶劳的过日子。王秋赫盼着年年搞土改,分浮财,享口福,在后来的极“左”路线盛行之下竟成为了现实。但好景不长,他在“文革”结束后,县委宣布撤销他的大队党支书和镇革委会主任的职务。他由此意识到自己的春梦已破,自己将永远退出历史舞台。于是他疯了,从一个红极一时的“运动根子”沦落为一个失意的“政治疯子”。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运动根子”王秋赫的政治掮客的本性,他好逸恶劳,不愿意老实地下地劳动,土改时分给他的好田地都搁置长起了荒草,工具也都生了锈。最后他开始偷偷暗地变卖土改时分得的胜利果实而且还每天盼着有朝一日又来一次新的土地改革,又可以分得一次新的胜利果实,因为土改他可以从中获得想要的利益,所以当李国香带领工作组进住芙蓉镇时,他会以李国香马首是瞻,两人勾结成为操纵芙蓉镇千百人生杀予夺的大权的父母官。胡玉音的家破人亡,秦书田的蹲监改造,谷燕山和黎满庚的挨斗罢官的惨痛遭遇都与他们有密切的关系。王秋赫是一个见风使舵的小人,李国香一手将他提拔为治安队长,在李国香红极一时,一手遮天时,他忠心耿耿的像一条哈巴狗,终日在李国香身边转,并与她将芙蓉镇搞的鸡飞狗跳,人仰马翻。但是,当李国香因身分不清被红卫兵批斗时,他将风舵一转带头批斗这个曾提拔他的“恩人”。而之后李国香因身份被查清,官复原职而且还升了官回到芙蓉镇,王秋赫又磕头又赔罪,最后又和李国香勾结在一起。王秋赫只是一个在运动中跟风的小人,他一昧追求自己的利益,保住自己,并不在意谁对谁错,他只想满足自己的欲望,所以在文革之后翻案时,他的美梦破坏,权利被收回,他就像普希金《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中的老太婆一样一切回归原点,不再辉煌。在这样的情况下王秋赫疯了,迷了心智。其实深究王秋赫可以说他是极左路线温床里培养出来的具有时代特征的毒菌,他是那个特定时代“那一类人”的代表。政治运动因为有了王秋赫他们才具备了发生发展的社会基础,而且王秋赫这些人也离不开政治运动,一旦离开了政治运动便会失去了生存的依靠,最终甚至会导致精神崩溃。所以从这点分析可以找到王秋赫之所以最后疯掉的深层原因。王秋赫的形象在当时社会是极为普遍又极具有代表性,他们在时势之变中追逐食、色和权势的贪欲时,其灵魂也在这种欲望的满足中而扭曲。他恣意追求内心的贪欲,恣意表演于荒诞的政治舞台上。我们可怜于他的下场,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像他这样的的卑鄙的跳梁小丑必将受到社会和人民的批判。三:极左路线下的人性扭曲《芙蓉镇》是一部“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的小说。小说中无论秦书田还是王秋赫都是那个特殊年代里本末倒置了的思想路线打造出来的令人啼笑皆非的人间悲剧。但再深究下去,造成这种结果的出现归根到底是由于当时极左的国家意志造成的,与其说是他们自己扭曲了自己的灵魂不如说是这个社会逼迫的,无论是出自自愿还是被迫。小说中的人物的兴衰沉浮完全由国家的政治政策决定的,当时的社会贯彻的是一条越穷越好,越懒越好,越左越好的极左路线。用被迫害致死的胡玉音的丈夫黎桂桂的话说,他们在农村贯彻的是一条“死懒活跳,政府依靠,努力生产,政府不管,有余有赚,政府批判”的错误路线。正是这条错误路线搞垮了经济,搞散了民心,进而把我国广大农村推向了一个十分贫穷,十分动乱,十分愚昧的危险境地。在极左路线的威逼下,人们胆战心惊,唯恐波及自己。但一些人还是避免不了,辛勤劳动的胡玉音夫妇,一个富有才气的知识分子秦书田,北方大汉谷燕山等一一遭到迫害。但是,运动红人王秋赫没有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有的只是旧社会的腐朽思想意识,这个淫词野调的流氓无产者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找到了表现自己歪才的舞台,他将芙蓉镇搞的乌烟瘴气。整个社会人心被掩埋,人性丧失,这让我们对王秋赫这种人感到可恨、可叹更感到可悲。为什么王秋赫这类人能被推到政治历史的舞台,这依然与当时的政治方向有关,他们在选拔干部时只讲家庭成份,不重视表现。有的人在领导运动时候,只看上级脸色,不顾实际,在组织生产的时候,只造政治声势,不管经济效益。王秋赫正好符合当时的时代要求,所以他能够在那个本末倒置的年代里,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过的是顺风顺水。但是,秦书田不愿意同流合污,但为了生存必须掩饰自己的本性,说一些口是心非的话做一些不愿意做的事。正如画家叶浅予在回忆录中所说的:“思想改造的目的就是改造人人都自觉地说假话,许许多多的人包括我自己,都是靠假话活过来的。”在这场运动浩劫中,数十万知识分子的良知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对于秦书田的遭遇我们感到同情,同时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来,在当时社会谁与党性和国家意志合拍,不管是非对错,谁就可以占据上风,占到统治地位,否则就会遭到不公正的待遇。回顾当时社会情形,对于所造成的结果我们无法去指责什么,整个社会的混乱,人性的丧失,每个人都在失去自我的情况下生存着。在外部政治的强大压力之下,整个民族呈现普遍失语状态,外部政治的强大显示着人性迷失。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纠正了极左的路线,还了他们的清白,但是留在他们心中的伤痕却永远无法消失。那段非人的岁月使许许多多人心有余悸,而小说中王秋赫的疯语:“五六年再来一次啊!”让人心惊胆颤,惊魂失语。四、结语《芙蓉镇》通过对秦书田、王秋赫等人的描述,深刻批判了极左的错误路线给人带来的灾难,它搅乱了芙蓉镇这块宁静偏僻的土地,也以强大的力量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尖锐得牵涉到人们的荣辱进退和身家性命。从这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愚昧对文明的戏弄,以及文明对愚昧的鄙视和颠覆。作者怀着高度的政治敏感在政治强光下折射人们内心的灵魂,反映了外在政治对国民心理的强行介入,国民性改造的时代课题又蒙上了一层阴郁的暗光,增加了人们的政治恐怖情绪。丑陋人性在政治照妖镜下得到了空前的大暴露,人们的攻击本能嫉妒心理,浑水摸鱼的心态获得了空前的释放,在匿名的掩护下堂而皇之的肆意作恶。人们的善良、同情、正直和爱心被可怕的掏空,同时也在历史创伤中抖落了国民性的伤疤。《芙蓉镇》正是通过这一极端的状态去映照人们心灵的暗角和政治的非比寻常,不合理的政治改变了人们的命运,正常的人性刻上了不同程度的暗伤。在这种极左的路线下,不合理的国家意志下,人性都完全扭曲。这部小说正是在向我们唱一曲有特殊的现实价值和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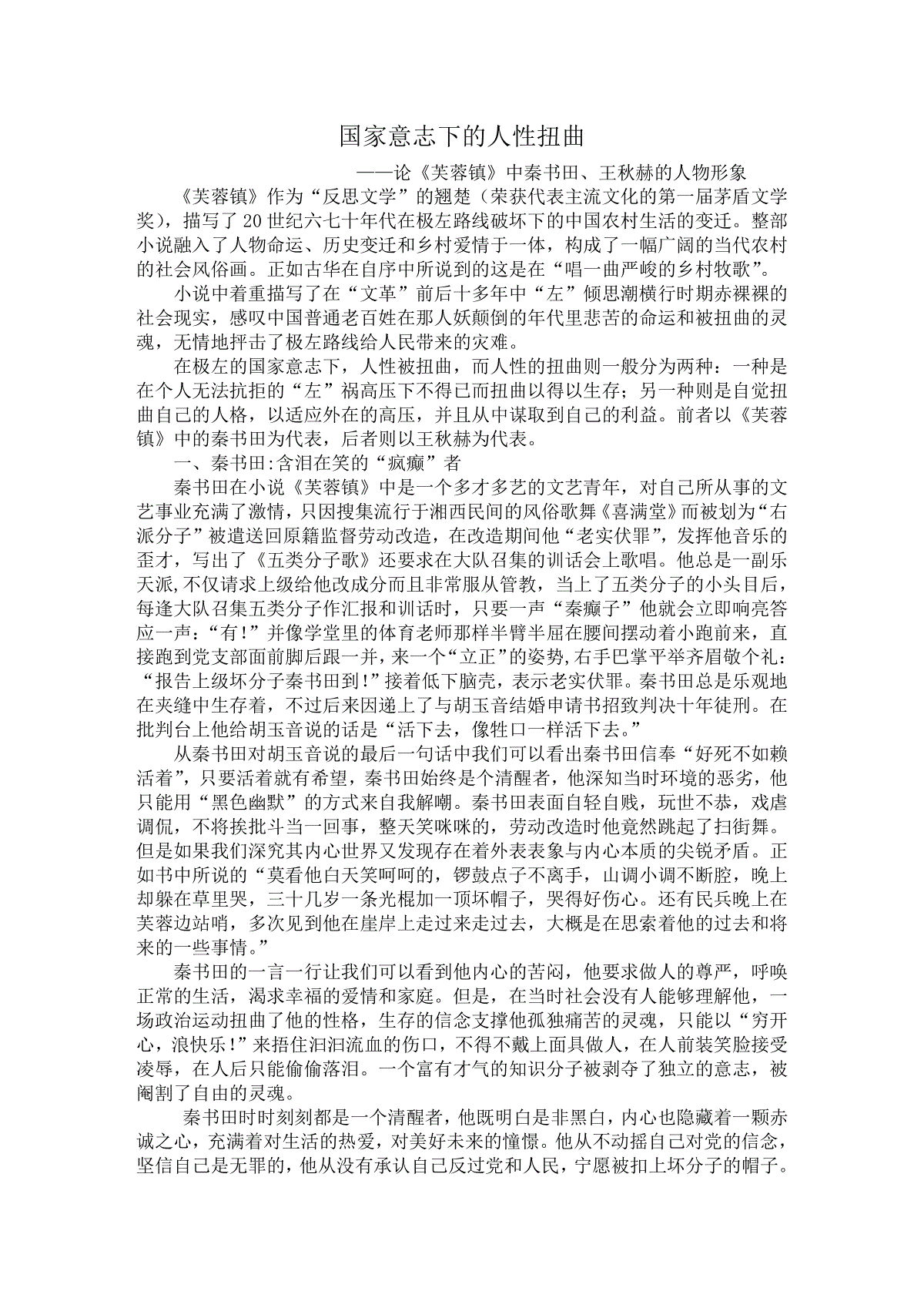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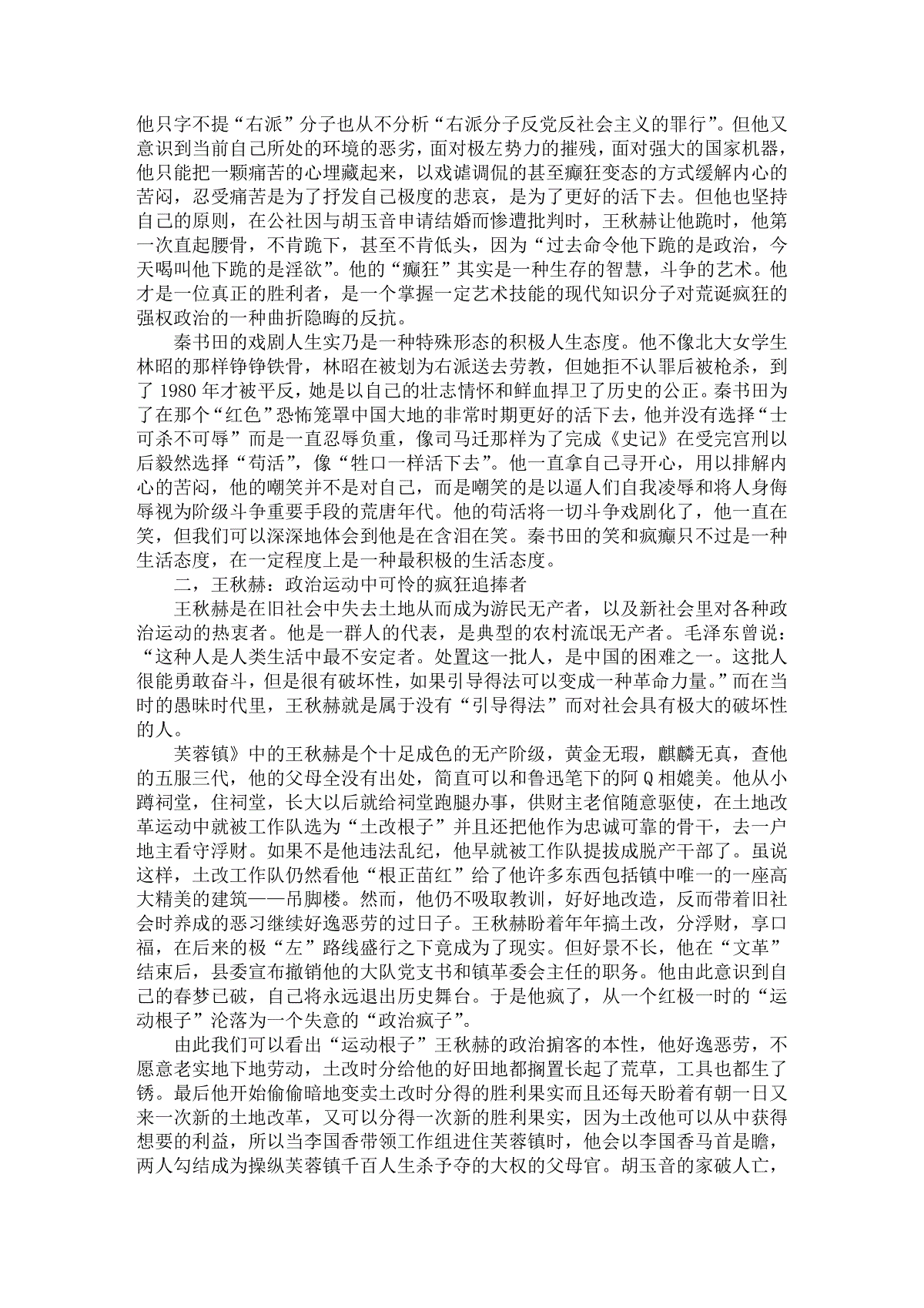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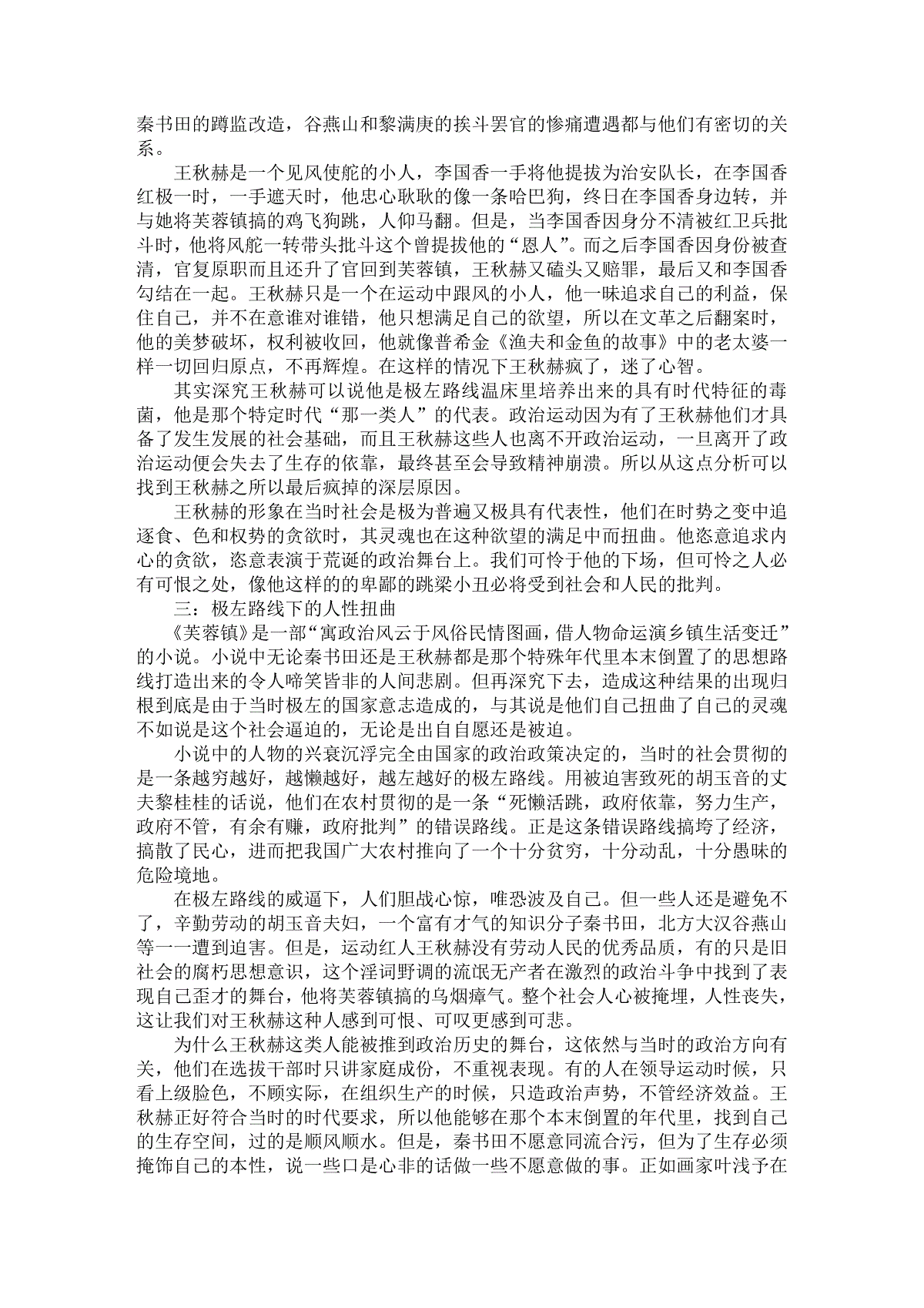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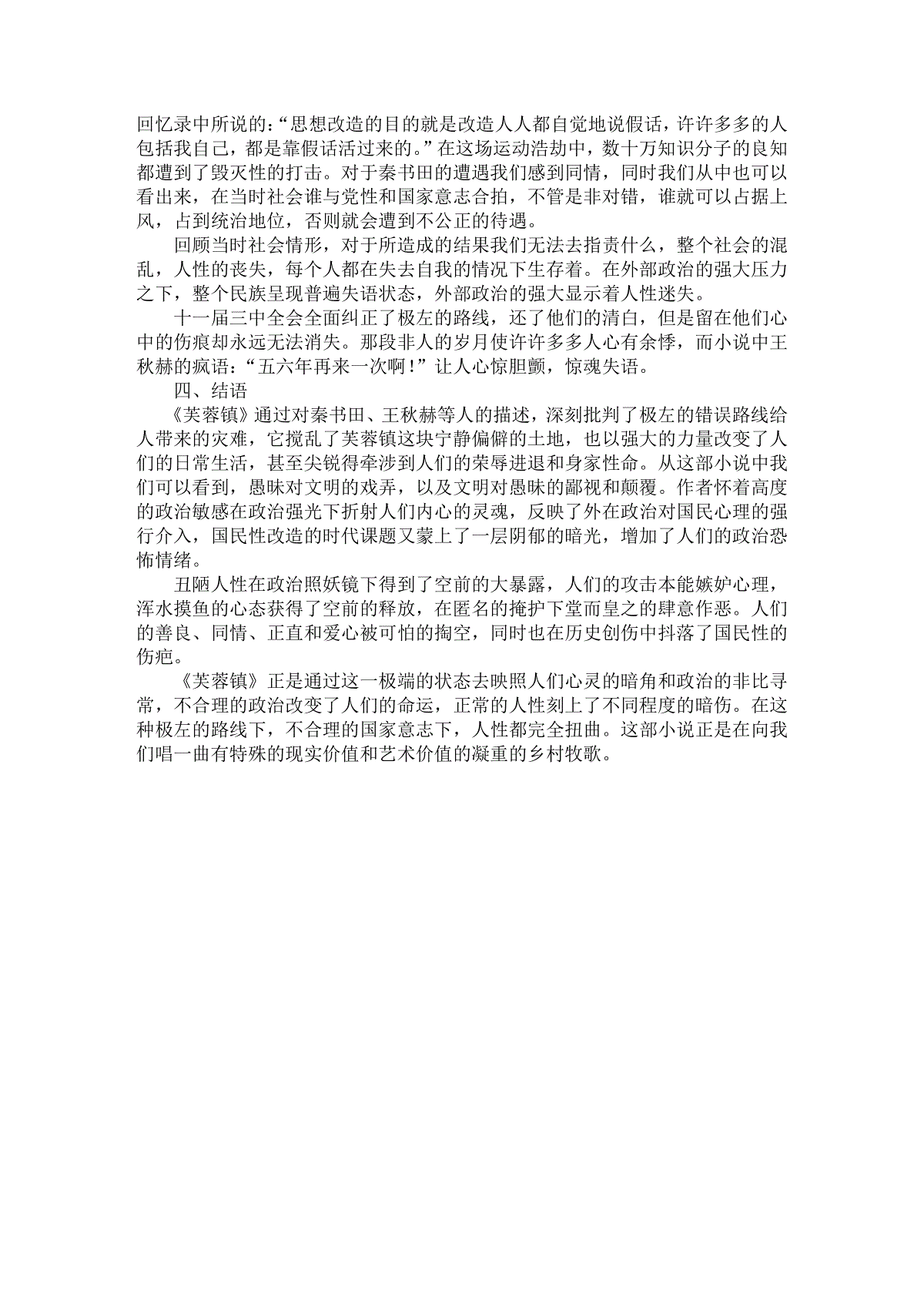
 三七文档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三七文档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kissanyb456
kissanyb456
共132篇文档
格式: doc
大小: 32.0 KB
时间: 2020-01-03
本文标题:国家意志下的人性扭曲论《芙蓉镇》中秦书田王秋赫的人物形象
链接地址:https://www.777doc.com/doc-2557925 .html